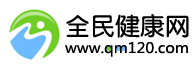,法律该拿你怎么办
题记:
上个世纪90年代,“”一词传入中国;2001年,西安,中国有了第一例案;2003年,武汉,中国有了第一例原告胜诉的案。司法界给这一胜诉案例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今后的司法实践以及完善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然而,个案的胜诉,不足以使“”案件的审判跃上坦途,摆在我们面前的现状是:的概念依然界定不清,,到法院立案依然困难,特别是最难的一环———取证,依然是决定这类案子胜负的瓶颈。
举证倒置未必可取
难取证不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
“有学者提出,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受害人很难取证,也就很难打赢官司。所以,应该把举证责任倒置,让加害人证明他没有实施行为。”
听了笔者的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给了一个让人没想到的回答:“屋里就俩人,举证倒置?这事鬼才说得清楚。”李教授笑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拿起手边的一个杯子,“我证明这杯子就不是我打的,怎么证明?举证责任倒不倒置都说不清,很多东西,想当然说一方道理时,是很有理的。说案件难取证,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道理讲不通。”
全都靠**录音取证,社会信用何在?
“不能倒置,那只有**录音取证了。”笔者小声嘟嚷着。
“也行,那你带一个取证,他也带一个,以防‘举证倒置’,”李教授没继续往下说,而是伸手往口袋里掏着什么,笑纹已经不由自主地显现在脸上。
他一手攥着从兜里掏出的一支小巧的录音笔,一手指着笔者放在桌上的录音机,边笑边说:“你看,你那儿有,正好我这儿也有。”他笑得脸都红了,“别担心,我这个没开。”
收住笑声,李教授严肃起来,“一个社会一盘散沙非常糟糕,现在一些地方就是这么一种状况,把过去的传统文化和西方值得借鉴的东西全否定了,这种情况下,让人们无所适从。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信任的话,只靠法律,靠人人都拿一个录音机,还能好得了吗?还像个社会吗?所以说,靠法律也要靠重塑社会信用。”
立法时机还不成熟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现行法律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个人的权利,不是说法律要一个个明文规定出来,我们不能把法律理解得这么僵化。
我们对法律有一种迷信,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立个法。一个固定的思维套路:问题的原因一定是法制不健全和打击力度不够,解决的办法一拍脑门就出来了,“加强立法、加强打击力度”呗。要我说,法律不能什么问题都解决。
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授:加强各法律中有关反的相关规定就行了
现在制定专门的反法时机还不太成熟。我认为,现在的刑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其实都可以为找到相关法律依据,加强各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就行了。
第一个提出为反立法的人———陈癸尊:反立法得一步一步来
立法将是个长过程,国外也是这么走过的。比如美国就用了22年。所以我觉得,目前分散立法也未尝不可。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来集中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估计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八年。
官司为何难打
一项调查显示,有71%的女性曾遭到不同程度的,但是,大部分以受害人忍气吞生告终。今年,走进司法程序的案件算是多的,然而,有报道可查的案件也没超过10件,在案件的海洋中,可谓“沧海一粟”。
这不到10件的案,也是负多胜少。案为什么这么难打呢?
原因一:在法律上没有界定
举个例子,有人在很多人面前讲黄色笑话或者有什么语言中的暗示,可能就是开玩笑,这是不是?有的人认为是,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
什么是?有的说就是“耍流氓”,有的说是“色迷迷的眼神”,有的说“也是”……
找遍中国现行法律条文,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出现过“”三个字。也就是说,一旦有人告上法庭,法官也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如何判定全凭他对法律的理解了。
专家意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授:绝不只**性,也有女男性和同性之间的扰。受西方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常指职场内男性对女性的扰。我认为,应该尊重受害人的感受,以一个中等文化水平、智力正常人的普通感受水平做标准。我想中国人是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客观中性的标准的。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我认为,如果在特定场景下(比如办公室),明显有尊卑位置的情况下,被扰人说扰了就是扰了。不是指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是这样的,那样就麻烦了,变成想诬告谁就诬告谁了。它的意义在于,提醒男性要与女性有一定距离。
原因二:案件,受害人难于取证
往往是发生在私下,而不是在公众场合;往往是利用职权,而不是使用明显的暴力;往往只有轻微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强迫实施,李楯教授一句“鬼才说得清楚”把取证之难形容得非常到位。
我国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既然根本就取不到证据,谁还会白费这份力气?
专家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民诉法教研室主任宋朝武教授:不可能是一次,第二次就准备好,带个取证设备,这种程序上有瑕疵取得的证据,只要取证的过程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可以被法院采纳的,而且越来越多的法院采纳了这种证据。
我们该做什么
用诉讼唤醒民众
“不能因为案胜少负多,就不打这样的官司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授说。她认为,这些案子胜败不是最重要的,败诉了实际上也是胜诉,胜在它起到了唤醒舆论、唤醒民众的作用。只要有这样的诉讼,胜诉就有希望。
设个专门机构
有资料介绍,国外许多国家都在政府下设一个类似于平等机会委员会这样的机构,集政府职能与司法职能于一体,专门处理案件。它的受案量大,程序简单,没有高昂的收费,也不用请律师。马忆南教授认为,“将来如果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写入禁止对妇女的条款,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保障实施。”
加强雇主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认为,在反方面,雇主应该做的事很多。比如:工作场所用半隔断的方式;领导办公室四周用玻璃墙,这些措施会很有用的。
马忆南教授说,国外对雇主责任规定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单位的规章制度里必须有防止的条款,发生了投诉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反别忘了农村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中的尤为突出,但是我们在制定法律时,对农村考虑得却不多。这是因为我们在法律上的话语,是从一些发达国家引进的,而他们的农村人口已经不多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
“不能造成一种人群歧视。”马忆南教授认为,虽然农村人口对可能不敏感,也可能还视为一种调剂,但立法必须考虑到农村。
取证难可以解决
11月23日下午4点,笔者如约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授家,马教授对问题颇有研究。
一开门,扑鼻而来的是一丝淡淡的中药冲剂味。开门的马教授鼻音很重,“昨天夜里有点不舒服,”马教授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的病情。书桌上,几本摊开的书旁,零乱地堆放着几盒药,这让笔者越发感到过意不去。
“用暗录方式取得的直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或许是身体上的不适,马忆南教授说话声音不大,但一开口便直戳要害:“证据问题是这类案件中最严重的问题。”案件的取证,因发生场所的封闭性或偶然性以及扰者的谨慎和权力等原因,要取得直接证据非常困难。“但是,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小巧的录音、录像设备的普及,获得直接证据的可能性不断加大。”
马忆南教授说,最高人民法院有个司法解释,将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限定为“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而采取暗录方式获得的证据并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且,对于扰者来说,没有什么“合法权益”被侵犯。
“我注意到,近来民事案件中,法院采用暗录方式获得的证据定案的情况越来越多,这将为案件的公正审理开启光明之门。”
“某些情况间接证据也可用。”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证明听到两人的谈话内容或争吵呼叫,这是一个证据;有人看到受害人衣衫不整、头发零乱跑出房间,这又是一个证据。但是,这些都是间接证据,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直接证据,法院是不会光凭这些定案的。
马忆南教授认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面对间接证据多而直接证据少或没有的情况,只要证据链条对事实能在相当程度上作出证明,就应该作出综合判断,认定事实的存在。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据标准对案件有点严。”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我国,不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诉讼,都适用这一统一的证据标准,“对案件来说,未免严了点。”马忆南教授的口气中多少透出些无奈之情。
“我国完全可以依诉讼类型的不同,实行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有必要降低证明标准,可以参考国外通行的“优势证据”标准确定,以缓和受害人的证明负担。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确认了“盖然性”标准原则。“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提出相反证据都无法否认对方证据时,由法院对其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高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也是解决取证难的一个办法。”
我国法律把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原告,也就是受害人。虽然审案时,法官多多少少也让被告举证,但在衡量两种证据时,还是要求被害方提出的证据一定是确凿的,一定要达到90%以上。
马教授认为,如果原告提供的间接证据已经达到足以对抗、否定、推翻被告不负有举证责任的状态时,被告自己提出的未扰对方的主张发生举证责任。某种意义上,他的举证责任程度已经超过了原告的继续补正的举证责任程度。
国外相关规定
美国1964年将写入人权法,1975年美国联邦法院第一次将定义为被迫和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1980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将定义为出于性需求而提出不欢迎的性行动、性要求或其他语言上身体上的。如果在屈服或拒绝之后,不明确地影响一个个体雇员的工作表现,或形成一个令其讨厌的工作环境,即构成。
2000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修改草案,建议15个成员国,对制定共同的定性标准。案件的被告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否则将受到惩处。那些对视而不见的企业,也将受到惩处。
2003年5月10日,欧盟委员会对这个指令进行了修改,修改对的定义是:是以对方非自愿的身体上或语言上的有性含义的进攻,造成损害对方尊言、名誉,给对方心理造成恐慌、敌意、耻辱的后果,这种性意义上的行为,从此以后是被禁止的,无论被扰者拒绝或是顺从最后都可以构成对扰者的裁决。
《瑞典平等法》中除了禁止雇主对其员工进行外,还规定雇主有责任调查员工提出的在工作地点发生的案件,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如果雇主不按上述规定办事,他就要在一定标准下对事件带来的损失负责。
法国规定,扰人应当受到纪律处罚,如果其同样是受雇职员,最重可以受到解雇级别的处罚,即刑事处罚一年监禁和15000欧元的罚款。采访札记 可怕的心理
本想采访几位案件受害人,但都没约到。
打赢中国第一场官司的武汉女教师何颖志这样说:“我以前是普普通通的人,以后还是,我希望过普普通通的日子,不想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雷曼———北京首例案的原告,干脆换了手机号码。
说实话,当初想找她们谈谈,无外乎想从她们身上多挖些“故事”。我到底想知道她们什么样的“故事”呢?无外乎那件让她们心灵受创的有关的“故事”。这一刻我才发现,其实我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心理罢了。正如一位专家所说:“我们总是盯住里面的那个‘性’字不放。”
以自己的行动为反法制的完善向前迈出一大步,她们做得已经够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在她们身上无限制地加砝码。
她们渴望宁静生活、有意回避媒体的选择理应得到尊重。如果换作我,也会选择这么做。
没有往常采访遭拒的沮丧,我反而有些庆幸。
相关链接
不该忘记的人
麦金农:美国法学家,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概念的人
1974年,麦金农女士受理一起一个女员工受到上级挑逗而辞职的案件。在那次案件当中,这位女士是由于个人原因辞掉这份工作的,按照美国法律,由于个人原因辞职不能得到社会救济。
麦金农女士认为,她个人辞职是因为她受到上级不公正待遇。既然起诉,在法律上必须对这种行为有一个定性。在当时,法律上没有办法定性,为此她提出来的概念。
陈癸尊:中国第一个提出为立法的人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癸尊第一次在立法机构中提出了“”问题。他在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时,提出应该增加利用职务之便对病人进行的惩处条款。
1999年3月,陈癸尊等32名代表正式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法》的议案。
何颖志:中国第一个打赢案子的当事人
她是湖北省武汉市某商业学校老师,被告盛某是她所在的教研室副主任。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对何颖志进行种种性诱惑。2002年7月4日,何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1万元。
今年6月,法院依据盛某给何丈夫写过的一份“保证”和一盘录音带认定,被告侵权事实成立。最终判令盛某向何颖志赔礼道歉。
部分案件一览
我国首例案:2001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一位国有企业女职员向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她的上司总经理对她进行了,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被媒体报道为我国第一次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件。
这件事情后来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当事人不仅败诉而且因此最终丢失了自己的工作。
我国首例胜诉案:2003年6月,湖北省武汉市女教师何颖志状告上司盛平案,何颖志一审、二审均胜诉,成为我国第一个打赢官司的受害者。
云南首例案:6月25日,云南首例女职工状告上司“”案件,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黑林铺法庭开庭审理。
四川首例案:陈芳(化名)被人强行搂抱抚摸后,被丈夫怀疑为“不忠”而常遭打骂。8月8日,四川省首例案尘埃落定,法院判决施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
河南首例短信引发的“”案:9月12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河南省首例因发短信息而引发的“”侵权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2000元精神损失费,并书面赔礼道歉。
浙江首例案一审判决:11月6日,浙江省温州市某调查事务所女职员谢某,状告该所负责人金某侵犯人格尊严纠纷一案有果。
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对原告的侵扰事实成立,须当面道歉,并赔偿5000元。
北京首例案原告败诉:11月6日,北京首例案以原告雷曼证据不足为由,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
北京一女士为20年前遭讨说法:自称20多年前遭上司多次,在向有关部门反映后,又遭到一连串的报复和威胁。12月1日,北京市的荆女士将单位告上了法院。
- 2008-03-25反立法不是“法律忽悠”
- 2008-03-25在中国
- 2008-03-25“”的由来
- 2008-03-25我国法律面对需要探讨的问题
- 2008-03-25如何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反法律体系
- 2008-03-25如何给“”定性
- 2008-03-25法律能有多大作用
- 2008-03-25,法律该拿你怎么办
- 1